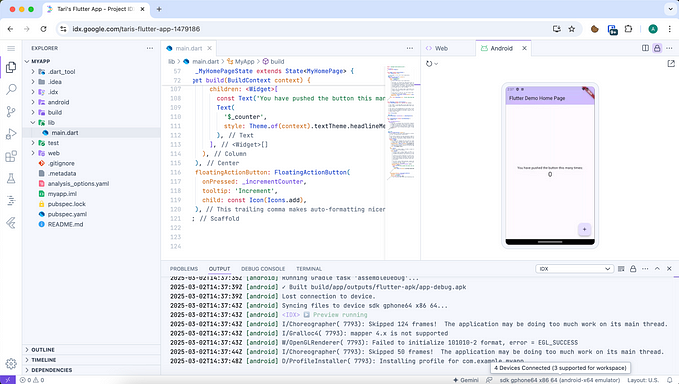群島譯作|傳統教育 vs 創新教育利弊談,反方:來自斯克魯頓的觀點
本文授權轉載自群島大學

來自顧遠的話:
最近,「群島客」社群裡湧現出了「閃翻共學活動」。這次閃翻的是一本名為《立場(Taking Sides)》的書,第一篇圍繞的就是一個極為經典的辯題:傳統教育 vs 創新教育利弊談。
在上一篇《群島譯作 | 傳統教育 vs 創新教育利弊談,正方:來自杜威的觀點》中,分享了代表創新教育一方 — — 杜威的觀點和論述,今天將分享來自反方斯克魯頓的觀點。
在閃翻後的共學中,顧遠分享了對正反兩方觀點的概括、論證方式的評論、以及背景信息的補充,這些將作為《傳統教育 vs 創新教育利弊談》系列的第三篇文章隨後發出,希望可以有助於大家更好地理解這個辯題,並形成自己的思考。
Enjoy reading~
傳統教育 vs 創新教育利弊談
學校教育是否應該基於學習者的社會經驗?
閃翻共學者:徐琛、麻吉、周賢、顧遠、Chloe、王晶琳、Sherry
■ 正方觀點
哲學家約翰.杜威建議,在更充分關注學習者的社會化發展狀態,以及他或她的整體經驗品質的基礎上,要重新考慮傳統的學校教育方法。
論述文章:《經驗與教育》(麥克米倫出版,1938年)

■ 反方觀點
英國哲學家羅傑.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表達了針對杜威的傳統人士觀點:進步主義教育強調「以兒童為中心」和「相關性」,對教育質量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
論述文章:學校與學校教育,《美國觀察者》(2006年6月)


在我11歲到17歲時,曾就讀於一所英國的文法學校 — — 這所學校由都驛王朝時期就被納入教育體系的一家基金會所創立,在戰後還依然維持著公共服務精神。
學校的老師們都畢業於老牌大學,他們有些在殖民地工作過,有一兩位在劍橋大學拿過獎學金,如果可以的話,他們大多寧願在學術上有更深的追求,而把擔任教職作為次優選擇。
有兩個重要的特點可以區分當年這些老師和後來的繼任者們。首先,當年的老師對「教育」一無所知,他們從沒有思考過教育專家、教育理念和教育實踐論的方法。在他們眼裡,教育專家的存在就像電視專家、髮型專家、水下籃球專家一樣荒謬可笑。
其次,儘管他們對教育一概不通,他們卻非常熟悉各自要教的學科。我們的物理老師曾和盧瑟福一起研究原子分裂,化學老師出版了一本關於碳氫化合物的教材,音樂老師是一位業餘的作曲家,也是我們當地一位有名的交響樂家Edmund Rubrra的朋友。教六年級英語的老師是F.R.利維斯(英國文學評論家)的學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T.S. 艾略特在創作《阿爾弗雷德·普魯弗洛克的情歌》期間就曾在我們學校任教,學校的圖書館也館藏了所有艾略特推薦的英語文學作品。我們的拉丁語老師,憑借著對維吉爾的痴迷感化了許多男孩,他還會用拉丁語和英語寫詩,同時他也是一位研究卡圖魯斯和葉芝的專家。
當然,你可以說這所學校是個例外。但它運營的原則卻不是例外,我們完全有理由假設,知識就是學校的業務,不論是公立還是私立學校,都要召募具備足夠專業知識的老師。
學校理所應當要確保老師在課堂上可以勝任一切教學任務,這也是基於這樣一種假設 — — 知識可以通過直接呈現的方式,自然地由老師作為展示者,傳遞給他的觀眾們,也就是學習者,除非這位老師有嚇人的吸血鬼牙齒或者口吃。這個假設總體來說,是正確的。
值得我們反思的是,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今天的公立學校都不再是過去那樣了。雖說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遺憾,但我們可以通過追溯不同地區教育衰退的原因,得出一些共同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教育學」這門學科的興起。關於到底應該教年輕的學習者什麼內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和昆提利安都曾對這一問題進行過諸多思考。但如今變得越來越常見的情況是,即便對某些專業知識一無所知的人也能成為教育專家。
舉個例子,教育專業的畢業生若要和盧瑟福一同競爭教物理的崗位,他可以理所當然地說:他的確非常瞭解物理,但我卻知道怎麼教物理。如今把「教育」當成一個專業,使得「無知者」比起「專業人士」有了無可比擬的優勢,而無知者和專業人士在人群中的比例是10比1。
不僅如此,教育作為一門學科,本身就是由顛覆者構建的。盧梭在《愛彌兒》中描述了一種全新的教學方式,而這些顛覆者們從中獲得靈感。他們認為知識的傳遞不該是權威的展示,而是一種輕柔的引導,因為大腦本身就處在知識的邊緣,渴望著學習,等待著被啓發。
但追隨者顯然沒有意識到,盧梭設想中的教學方式需要一位昂貴的私人導師,每天進行一對一的輔導,而這本身也使得導師根本沒有時間去學習他應該傳授的知識。
還有一位抱有許多荒謬觀點的人物,對學校教育有著很大影響,他就是約翰.杜威。杜威主張教育應該去權威化,要鼓勵兒童在自我表達中發展。他認為真正的教育主體應該是兒童,因此不該把焦點放在教師身上。
這種「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旨在通過喚醒、引導和鼓勵的方式支持兒童探索世界,因此教師需要提供與兒童本身的興趣相關的素材,並激發他們主動思考。
於是,學校教育中出現了兩種摧毀性的理論:「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和「知識的相關性」。
恰逢狂熱的平等主義者們一貫憎惡學習,在他們看來學習只會把人分作三六九等。現在這些人又多了「兒童中心教育論」和「知識相關性」這兩樣理論,他們在反對知識學習的戰鬥中就更加得心應手了。
這場爭論在60年代的英國有了一個新的發展趨勢。我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教育學」的老師們,當時唯一的資質要求就是具備專業知識,而反觀那些進了師範學院的人,大概率是些考不進其他專業、除了「教育學」再沒有其他選擇的人。所以當要和真正掌握了專業知識的畢業生一起競爭工作時,他們明顯沒有什麼拿得出手的,不過這反倒省去了場面上的廢話。
「教育學」之所以能成為超越專業知識般的存在,甚至具有無法被超越的優勢,全賴哈羅德.威爾遜那屆社會主義政府提出的一項狡猾的政策。他們推出了教育學研究生學位,為所有想進入教育體系工作的專業人士強加了一道障礙。除非有一年額外的教育專業學習,否則只在某門學科有競爭力的畢業生是不被允許在公共教育體系裡任教的。其實這一年都稱不上是學習,只是一段糊弄又官僚的灌輸過程。這些佼佼者們聳了聳肩,選擇了其他工作。
為了適應「與兒童有關的課程」,考試制度也被重新設計。好老師開始被體制驅離,理由是他們對兒童的需求「不敏感」,能教的知識也是對兒童來說不實用、與他們的經驗不相關的。
當有人指出如今30%的英國兒童到畢業還無法進行閱讀與書寫時,教育家們解釋道,在資訊時代,學生不需要發展讀寫能力。沒錯,如今資訊被隱喻為知識的敵人,滿屏都是大量未經分類的事實與信誓旦旦的編造,像瘋人的獨白一樣鋪天蓋地。但並不能以此就認為,學生無需掌握讀寫。
這樣的「教育」幹倒了知識,即使是法國、德國和美國也是這樣:「所有可進入學校的知識其目的都是為了兒童的生長」,這已成為不被挑戰的信念。
而我的老師們則持有相反的觀點:所有進入學校的兒童其目的都是為了獲取知識。孩子們在教室裡就是不應該進行「有用的」學習,真正的知識就是與小孩子的世界沒有直接關聯的。
知識的價值就在於純粹而無用。像和聲與對位、拉丁語與詩歌,量子力學定律和超限技術理論 — — 這些知識本身就是其存在的理由,不需要屈服於實用。
兒童能把知識帶到未來,他們會攜帶著這些人類智慧的結晶繼續生活,甚至還會繼續添磚加瓦。用其他方式來對待知識,在我的老師們看來就會導致知識的消亡。他們是對的,知識的確正在消亡。
迄今英聯邦發起的意在遏止知識消亡的嘗試都將是徒勞的,因為這還是由教育家們主導的。倒是美國人發起了「在家上學」的運動,他們是對的,這是從國家插手教育以來我看到的第一縷希望。
當一位母親坐下來教她的孩子時,她會本能地意識到她的角色就是傳遞知識。她不會以自己教的是否與孩子相關,是否對孩子實用為標準來評判自己。
想想看,對孩子來說,沒什麼信念比「地球是平的,所有孩子都是受害者,你的就是我的,2+2=5」更有用的了,也沒有什麼比「魔法與超人、動畫片和網絡流行語」與生活更息息相關了。可這些都不會出現在「在家上學」的課程中,因為在家上學的本質,是致力於傳承父母認為有價值的知識,孩子是否已經感到了關聯性並不重要。
我的願望是,隨著越來越多的父母迎接了這份挑戰,隨著他們逐步學習鏈接資源、分工協作、分享專業技能和知識,已經從常人世界中消失了的珍貴東西 — — 「學校」又會出現。
就在離此地不遠的弗吉尼亞州鄉村,有一間廢棄的舊屋,裡面有一間教室、一間小廚房和一間廁所。如果你望向窗外,會看到藍嶺山脈(BlueRidge Mountains),遠處是老破布山(Old Rag),近前是一兩匹馬。教室裡有一塊黑板、一個書架和幾張破舊的課桌。
從沒有教育家涉足這裡,也沒有官僚知道它的存在。只要再有一兩個孩子,一兩個成年人,只要他們在一起,就會自發地生成對知識的熱忱,而文明的產生恰恰是從這些不需要投入經濟資本的地方開始的。
(《學校與學校教育》,發表於《美國觀察者》2006年6月刊)
附錄
教育是為了智力訓練還是社會化發展 — — 杜威和哈欽斯的爭論起源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之爭,直到今天亦無定論。心理學家、社會學家、課程專家和大眾評論家們也紛紛發表各自的觀點。
杜威的追隨者認為,智力訓練不能脫離其他發展因素,事實上,關注學習發生時的具體情境能進一步加強智力訓練的效果。
而杜威的反對者則擔心,學校教育就是為了系統性地獲取知識,如果花費精力關注在學習者的社會化發展上,將減損學校教育的獨特價值。
進步主義運動到底給教育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還是為未來的教育發展奠定了基礎?歷史學家勞倫斯.克雷明在《學校的變革》(1961) 裡有更中肯的評價。美國六十年代的「自由學校運動」也部分起源於進步主義教育觀,Allen Graubard在《解放兒童》(1973)裡對此亦有分析。Diane Ravitch撰寫的《動蕩的教育運動》(1983)和Mary Eberstadt撰寫的《他們應得的學校》(發表於《政策回顧》,1999年10/11月刊)對進步主義也提供了有價值的評述。
在教育哲學方面,有三部著作也值得推薦,分別是:GeraldL. Gutek的《關於教育的哲學思想觀點》(1988),Edward J. Power的《教育哲學:哲學、學校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1990),以及Howard Ozmon和Samuel Craver合著的《教育的哲學基礎》(1990).
同樣值得一讀的還有PhilipW. Jackson在1996年夏季教育論壇上發表的《重溫杜威的經歷和教育》,Jerome Bruner在1996年出版的《教育文化》 — — 特別是第三章《教育目標的複雜性》,Christine McCarthy刊登在《教育理論》1999年夏季刊上的《杜威的教育倫理:哲學或科學?》,Debra J. Anderson和Robert L. Major合著的《杜威、民主與公民》(發表於《The Clearing House》2001年11/12月刊),Julie Webber的《為什麼我們不能成為杜威那樣的公民?》(發表於《教育理論》2001春季刊),David B. Ackerman的《新世紀的根基:挖掘傳統教育和進步主義的精華》(發表於《Phi Delta Kappan》2003年1月刊),以及William Hayes所寫的《進步主義教育的未來》(發表於《教育水平線》,2008春季刊)。
留給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能否跨越非此即彼、兩極分化的觀點之爭?如果要設計出有價值的教學過程,教育者是否必須對高屋建築的教育理念和目標有清晰的理解?以及一線教師們要如何落地這些高屋建築的教育理念?